阴阳和五行是中国文化的基本构架。你同意也好,不同意也好,说它好也好,说它坏也好,无论如何中国文化都摆脱不了阴阳、五行的影响。在这里,我们把五行作为文化现象简单地介绍一下。首先应该注意的一点就是,千万不要用科学来研究五行。
五四时代,人们就是以科学为标准来分析五行,因而认为它是不科学的迷信。事实上,五行本来就不是科学,它是一种文化。它之所以不是科学,也正因为它是一种文化。我们不能因为它不是科学,就置之不理。五行这个框架,是中国人无法摆脱的。所以,我们把它视作一个文化现象,视作一个了解中国文化的很重要的切入点。
一、五行之前:
五与六竞争至尊地位
我们先说“五”,然后再说“行”。数字共有十个: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。对中华民族而言,这十个数字里面,最得宠,最为大家认可推崇的大概就是五。南美洲的一些民族喜欢四;日本人喜欢三。而我们这个民族的的确确最喜欢五。原因很简单。因为人有十个手指、十个脚趾,每一只手或脚上各有五个指头。不过,五也是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,才得以确立如此崇高的地位。
跟五竞争的大概是六。为什么六敢来竞争呢?这跟天文现象有关。地球有一颗卫星,叫作月亮。月亮绕着地球转,每年转十二圈,形成十二个月。因此,十二这个数字就显得非常神圣。十二是两位数,其基数为六。六与天象有关,得天时;五跟人体有关,得人和。所以,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,人们无法确定五与六到底谁更尊贵一些。
在《国语·周语下》里面,有句话说:“天六地五,数之常也。”五和六是常数。有人把“天六”,解释成“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”。文献中有“天有六气”的记载。哪六气呢?就是阴、阳、风、雨、晦、明。在没有任何文献背景的情况下,我们也可以不把“天六地五”的六解释成六气。作为“数之常”,这里说的只是六、五两个数字。所以,我们可以把六理解或想象为上面提到的天文现象,即月亮与地球的关系。
在《国语》中,天六居首,地五居次。此外,大家都知道“天干地支”。天干是甲、乙、丙、丁、戊、己、庚、辛、壬、癸,一共十个;而地支却有十二个。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是十二地支,十个天干;而不是十二天干,十个地支。简单说吧,在五备受推崇的同时;数字六的地位也非常显赫,有时甚至还取得了优势。“天六地五”的语序就说明了这一点。据现有资料来看,大概在春秋时期,五跟六的位置还很不确定,二者仍处在竞争之中。
《左传·文公七年》引《夏书》说:“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、谷,谓之六府。”府就是收藏东西的地方,也就是储藏室。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,加上谷——庄稼和粮食的总称,合称为“六府”。就是说,天下万物都可以储藏在这六种东西里面。请注意,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就是现在我们所知道的五行——五种元素。而谷不是原始的自然元素,是被创造出来的。我们可以将前五府视作自然元素,而第六府则是人造的第二自然。把谷与水、火、金、木、土并列在一起,在观念上有些杂乱,其抽象度显然不高,所以,应该出现得比较早。虽然我们不能确定其具体时间,但是依据思想发展的逻辑推断,六府观念早于五行。在五行确立以前,六与五互相竞争。后来,五慢慢占了上风。
二、五行的涵义:
元素、能量与德行
行这个字,麻烦更多。行的本意是道路,在甲骨文里写作【五1】,
就是十字路口。这是一个具体的东西,但同时强调了通行的意味。一条路就可以通行,所以十字路口暗示了四通八达,着重于行的动词意味,即,前进、行进。可见,行有两层意思,一个是道路;另一个是行进。因此,五行的行也应该有两层意思:第一,它是物质元素;第二,它处在运动中。大家一定要认识到第二点的重要性。西方人翻译五行时,往往把握不住“动态”这个内涵,所以大多翻译成“Five Elements”。Element是元素,并不包含动态的意义。后来李约瑟建议,改用“Energy”来翻译,译作五种能量。能量的能,就把行的动感表达出来了。
在中国,五行的行,除去上述“物质元素”和“运动之中”这两层意思之外,还有一层更重要的意思,那就是“德行”。这三种意思长期混杂并行。严格地说,五种德行并不是我们要讲的五行的主要内容。可是,在文献中最早出现的,恰恰是五种德行。
《尚书·甘誓》篇据说是夏禹王的儿子在攻打有扈氏前发布的誓词。打仗之前,把队伍召集起来,进行动员说:我现在要去攻打有扈氏。为什么?因为他有两大罪状:一是“威侮五行”;二是“怠弃三正”。前人总是对此困惑不解。因为一提到五行,大家就想到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。可是,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这五种东西怎么能够被“威侮”呢?一个人能够坏到“威侮”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地步,这确实让人感到不可思议。既然大家都不明就里,有些人就大胆臆测,以至于出现各种各样的解释。
后来,我们才搞清楚,这里五行的行应该念héng。现在以行为字根,读为héng的字很多,如:珩、桁、胻、烆。可是,很奇怪,作为这些字字根的行,在现代字典上却没有héng这个读音。我认为,有扈氏所“威侮”的应该是五行(héng),指的是五种德行(héng)。现代口语说的道行(héng),实际上就是德行(héng)。说某人道行很高,其实就是说他德行很高。有扈氏“威侮”了五种德行,所以招致讨伐。哪五种德行呢?就是我们后来在马王堆帛书里看到的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。
关于帛书中的五行,我们这里先简单提一下,以后再具体讲。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是五行(xíng);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是五行(héng)。至少在西汉以前,人们是很清楚这个分别的。从五行(héng)到五常的演变过程就印证了这一点。我们之所以知道仁、义、礼、智、圣是五行(héng),就是因为它后来变成了五常。以“常”字代替“恒”字,是汉文帝时期的用法。汉文帝叫刘恒,为了避讳,就把所有的“恒”字都改为“常”。恒山改叫常山;姮娥就叫嫦娥;而五行(héng)就变成了五常。直到董仲舒时代,人们都非常清楚这一点。
我们现在读董仲舒的《春秋繁露》,会觉得有些地方非常费解,比如“故五行者,五行也”。如果不知道五行(héng)的读音与意义,这个句子就解释不通。假如我们把两个行都念成“xíng”,“故五行(xíng)者,五行(xíng)也”。天下有这么写文章的么?同语反复,到底是什么意思?其实,这句话应该是“故五行(xíng)者,五行(héng)也”;或“故五行(héng)者,五行(xíng)也”。两个行分别指两种东西:一个说的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,另一个说的是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。董仲舒认为,我们之所以要提倡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,是因为世界的基本规律就是五行(xíng)。仁、义、礼、智、信这五行(héng)跟天地之间的五行(xíng)是对应的。只有搞清楚五行(xíng)与五行(héng)的不同读音与含义,我们才能真正读懂《春秋繁露》。
三、五行的起源:
甲骨文中的“五方”
清楚了“五”和“行”这两个字的意思,我们就可以把二者合起来,探讨五行这个范畴。五行的最早形态是五方,或者说,五行起源于五方。五方就是东西南北中五个方位。每个人以自我为中心,确定出东西南北,再加上居于中心的自己,就形成了五方,这大概是最早的五行思想。我们现在看到的商代甲骨文几次谈到五方:说东方怎样、西方怎样、南方怎样、北方怎样,最后说中方怎样。中方有时候也写成“中商”,是商人对自己的称呼。
商代人为什么如此重视五方呢?这跟商人的游牧生活方式有关。总的来说,农业民族比较重视“时”,游牧民族比较重视“方”。或者说,前者比较重视时间,而后者比较重视空间。农业民族必须搞清楚时令,否则错过播种时间,庄稼就不长了;错过收获时间,粮食就全掉在地上了。可见,时间观念对于农业民族很重要。而空间、方位观念对于游牧民族则具有非同一般的意义。游牧民族赶着牛羊四处放牧,如果没有明确的方位观念,晚上就回不来了。周人是农业民族,这已有定论。商人虽说并非完全不种庄稼,但是他们更多地依赖游牧生产方式。所以商朝人搬来搬去,迁徙了好多地方。作为游牧民族,他们非常重视方位。
在甲骨文里,我们看到东方、西方、南方、北方;也看到西方的风、东方的风、南方的风、北方的风;还看到西方的帝、南方的帝、东方的帝、北方的帝等等类似的观念,其中出现最早的是五方。确定了五方,然后把这五个方位拟人化,想象成五个不同的“帝”。东边的帝叫作青帝,南边的帝叫作炎帝或赤帝,西边的帝叫作金帝或白帝,北边的帝叫作黑帝,而中间的帝就是黄帝。
这个思想不仅出现在甲骨文里,传世文献中也有记载。《墨子·贵义》篇里有一个关于五帝的有趣故事。有一天墨子从南往北走,在路上碰见一位“日者”。日者就是根据天象算命打卦的人。日者对墨子说,你今天最好不要往北面去。为什么?因为今天天帝要“杀黑龙于北方”,“而先生之色黑,不可以北”。墨子整天在外面跑,脸晒得很黑。他被称作“墨子”,估计跟脸黑也有关系。日者说,你的脸太黑了。今天天帝正在北方杀黑龙呢,你往那儿跑,可能就顺手把你杀了。墨子当然不相信,坚持前行,最终平安归来,还跟这个算命的辩论了半天。《墨子》的成书年代比较晚,大概已经到了战国时代。可是这个故事所反映的思想还是最早的,方位意义上的五行。
除此之外,在《山海经》、《吕氏春秋》等书里面,也有东方神、西方神、北方神、南方神这些概念。东方的神叫句芒,南方的神叫祝融,西方的神叫蓐收,北方的神叫禺彊。这些名字有的可以解释;有的不好讲。自古以来,有些人名有特别的意义;有些人名只是个称呼,以示区别。如果一定要解释的话,我们姑且认为,东方代表生,所以叫句芒(即,句萌);南方代表长,祝融跟火有关;西方跟收获有关,秋天是收获的季节,所以叫作蓐收;北方跟保藏和水有关,但是我们至今不知道它为什么叫禺彊。在甲骨文里与五方、五帝、五神、五风同时出现的,还有五火。我对它的解释,请大家参考《火历》一节。总而言之,五行是从五方开始的;而五方之所以受重视,跟商人的游牧生活方式大有关系。
四、五行的确立:
从五材到五行
五方进一步发展,就落实到五材上面。五材,就是五种材料。上文提到,西方人把五行翻译成“Five Elements”,就是侧重于材料这层意思。中国人的确曾经在一段时间里,更明确地把五行视为五种材料,或者说五种元素。我们迄今所见最早明确指出五材就是金、木、水、火、土的文字,出自《左传·襄公二十七年》:“天生五材,民并用之。”天生出五材,这五种东西老百姓都要使用,不能只用一种;也不能偏废其中的任何一个。就是说,这五种材料是人们生存、生活、生产的必需品,缺一不可。这个五材说比较明确,也比较符合逻辑。五种材料都是天生的,跟混杂了属于第二自然的谷的六府说大不一样了。可见,在春秋晚期,五行思想已剥离掉包括谷的六府概念,演变、升华成五材的观念。
此后,五材逐渐转变为五行。我们迄今所见最早使用五行一词的文献是《尚书·洪范》篇:“初一曰五行”,又说“五行:一曰水,二曰火,三曰木,四曰金,五曰土”。《洪范》里一共谈了九个大问题,也就是治理国家的九大基本法则。其中“初一曰五行”。第一大法就是五行,把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上。可见,在讨论如何治理国家、安定社会的时候,古人首先想到的是宇宙的形成、万物的生长,这是从宇宙论、世界观的角度来提出五行。因此,在诞生之初,五行的地位就十分明确重要。前面提到的五材、五方、五风、五火、五帝,都是非常具体的东西。而五行则是治理天下的九条根本大法中的第一条。这说明,当时的人已经清楚地认识到,五行是关于宇宙观的一套理论。
请注意,《洪范》中五行的排列顺序是: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;它们对应的数字分别是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;以及第二次循环的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是五行的生数;六、七、八、九、十叫作成数。这是一个非常经典的排序。但是,在这种顺序下,五行之间既不是相生关系,也不是相克关系,更不是循环关系,毫无章法可言。对此,后人提出了一种解释,叫作“由微及著”,就是从不明显到明显,从小到大,从少到多。水最少,然后火稍微多了一点,然后变成木、变成金、最后变成土。土当然最大了,因为整个地球都是土。仔细分析的话,我们就会发现这种理解太牵强。如果“由微”开始,火应该是最“微”的。水还能被舀起一碗呢。而火是没有形状,抓不着的。人一动它,它就跑掉了。所以,火、水、木、金、土的次序似乎更合理一些,可是《洪范》里却是水、火、木、金、土。
后人在谈到五行时,可以有各种理解,也可以按照不同的需要来排序。但是,五种元素分别对应的数字却几乎是固定不变的。比如,提到水,人们马上想到的就是一和六;土就意味着五和十。所以,我们有理由推测,最早确定五行顺序及其对应数字的就是《洪范》。此后,所有谈及五行的人都接受了《洪范》的观点。这说明《洪范》中的五行观念出现得最早。
大家可能听说过浙江宁波的藏书楼天一阁。它之所以叫天一阁,是根据《易传》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”来命名的。到过天一阁的人都会发现,它是六间房的开间。这在中国是非常特殊的。在其他地方,开间大多是单数。比如说,故宫是九开间,一般人家是三开间。其实,无论是天一阁的名字,还是六开间的格局,都源自“天一生水,地六成之”。为什么呢?藏书最怕火。要想制住火就得用水。储水当然要用水缸了。于是,就盖一栋六开间的房子,并把房子涂成黑颜色,起名叫天一阁。黑色代表水;六开间代表“地六成之”;天一就是“天一生水”,一切都是水,所以这个地方就不会着火了。此外,承德有个藏书楼叫文津阁,与天一阁一样,也是六开间。后来,人们还试图把八卦及音乐中的五音十二律与五行联系起来。宫、商、角、徵、羽五音可以与五行一一对应。不过,我们很难确定十二律、八卦与五行的对应关系。
世界其他国家的古代哲学中也有类似五行的概念。印度哲学有“四大”,分别是地、水、风、火;而希腊哲学的“四大”则是火、气、水、土。这两种“四大”观念差异不大。在印度叫作风的,被希腊人换为气。其实,风就是气,气就是风。尽管印度人和希腊人也认识到了几种元素,但是他们的四大里缺金。说实话,金这个东西呢,尽管后来很重要,但是在人类社会的早期无足轻重,因为人们利用不了它。金就是能够冶炼出金属的矿石。如果人类的生产能力没有达到一定水平,就不能冶炼矿石,它就没有用。这就好像铀一样。现在铀不得了,是制造原子弹的原料。但是在若干年前,它一点用处也没有。因此,印度、希腊只谈四大而忽略了金,是可以理解的。中国的五行观念包括金。这说明,在五行观念出现时,中国的发展程度已经比较高了,人们开始加工利用矿石。也就是说,矿石是“民并用之”的“天生五材”之一。这是需要注意的第一点。第二点就是,印度也好,希腊也好,它们的“四大”本身不会动。希腊人认为:世界上有两种力,一个叫爱力;另一个叫恨力。爱力使四大结合,恨力使四大分离。爱力、恨力是作用于四大的外力。而中国的五行,既是五种物质,又是五种运动变化中的东西;五者之间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联系。
(未完待续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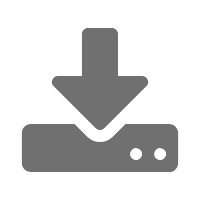 天机APP下载中心
天机APP下载中心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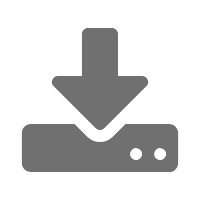 天机APP下载中心
天机APP下载中心